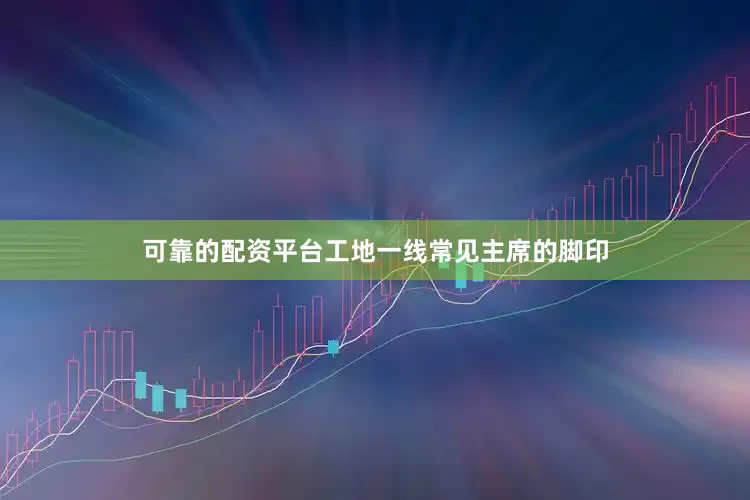
“1947年深秋的午后,方丈忽然抬头提醒:‘主席,黄河谁都能下水,您却万万不可。’”一句看似随口的劝告,把刚刚取得沙家店胜利、准备登高赏景的毛泽东拦在白云山寺外的台阶上。
战争正炽,延安周边兵荒马乱,毛泽东难得吁口气,他本想顺着寺旁栈道俯瞰黄河。黄水滚滚,浪头拍岸,令人胸臆生风。“湘江我少年常游,长江也渡过多次,这条母亲河改日试上一回。”他平静道。李银桥在旁边点头,没料到方丈立刻摇起手。

老和尚捻珠,语速并不快,却字字分明。“黄河属土,主席五行亦重土,土重则沉,黄河的急流与泥沙会将您拖入深涧。”理论带着玄学味,现场却没人敢笑场。毕竟正逢战局关键,任何安全隐患都得掐灭。
毛泽东望着河心若隐若现的乱石,唇角一挑,说了句“多谢提醒,且记下”便作别寺门。事后李银桥悄声问他到底信不信。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,只留下一句:“凡事以人力可为,不必拘神鬼。”随后翻身上马奔赴米脂。
表面上一场插曲就此结束,实际上,这番交谈像一粒沙子,悄悄嵌进毛泽东心里。几年后新中国成立,治理黄河被正式摆上中央议程。一纸命令,水利专家、部队官兵与沿岸群众陆续集结,勘测、打桩、筑堤一气呵成。
资料显示,1950—1952年间,中央直接拨付的治理经费超过20亿元,那是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还多。有人回忆,会议室里刚讨论预算时,部委干部掰着手指数零,气氛紧张。毛泽东只说一句:“黄河不安,中国难安。”话落,资金拍板。
工地一线常见主席的脚印。茫茫风沙里,他蹲在土埂边捻起黄泥,半开玩笑:“看上去是祸害,其实都是肥。”水利队员将细沙倒进量筒,讲解含沙量,主席时而插话:“沉降区该不该留作淤地?一年能长多少土?”一句句追问,让在场工程师暗暗叫苦,却也逼出后来的导洪分流方案。

1954年夏汛,黄河花园口水位逼近警戒线。堤内百姓望着漫天浊浪惴惴不安。电报飞进中南海,毛泽东批示:“人退一步,水进两步;人进两步,水退一步。”防汛大军连夜顶上。洪峰过境,花园口没失守,沿岸仅零星漫溢。民众说,这仗打得不见硝烟,却同样凶险。
历次视察,毛泽东都想跳进河里一游。1956年秋,他站在三门峡初步选址点,望着仍自由奔腾的黄水,两次推脱警卫递来的防水靴。队伍里有人打趣:“主席又想‘中流砥柱’了。”终因技术人员报告水下旋涡,计划被叫停。
1966年夏,他借武汉畅游长江之际,再次提起黄河。那年气候反常,黄河多年未遇的凌汛提前,安全部门不敢松口。毛泽东听完汇报笑言:“黄河我迟早要下去,不急这一时。”语气平淡,却不掩失落。
对黄河的情感,并非兴之所至。延安时期,毛泽东亲眼见到黑龙港一带的漫滩荒芜:麦苗刚出土即被泥水埋没,牛羊躲在高坡哀叫。老百姓抄着木盆刮泥找粮。那情景深植脑海,后来“要让黄河成为真正的母亲河”这句话,多次出现在他的谈话、文件和诗稿里。
有意思的是,与其说他畏惧老和尚的“五行相冲”,不如说顾虑另一个现实——时局。黄河两岸是北方交通要冲,一旦安全工作稍有疏漏,不仅个人安危,国家指挥中枢也可能陷入被动。李银桥晚年回忆:“主席水性好到惊人,可凡事牵连太大,他常主动克制。”

1974年重阳,毛泽东身体已不比当年。黄河治理基本告一段落,三门峡、刘家峡、青铜峡梯级发电站正在并网。他在书房里听完水利部汇报,轻声念了句“九曲十八弯终被制服”。身边医生提醒要休息,他却要求再看一张黄河治理示意图,目光停留良久。
那一年,白云山老和尚早已圆寂。寺院新任方丈重修经楼,在旧纸堆里发现当年招待中央首长的茶盏。盏底墨迹犹在,写着“土可孕生万物,亦可吞人”。消息传到北京,知情者笑道:“和尚其实在劝主席敬畏自然。”

黄河仍在奔腾。泥沙依旧,每年携带量超过十亿吨,但决口次数大幅减少,沿岸百万亩农田稳产高产。站在今日的数据面前,世人才渐渐理解,那场关于“能不能下水”的对话并非迷信与理性之争,而是国家领袖对自身责任的权衡。
毛泽东终究没有游过黄河,却让更多人得以在母亲河畔安家落户、放歌劳作。对许多上了年纪的北方汉子而言,这远比看他纵身一跃更解渴、更踏实。
2
十大炒股杠杆平台排行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什么炒股软件可以杠杆等到你开始用了之后发现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
